书摘:孔子的平凡与伟大

在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像孔子那样,能够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评头论足、津津乐道长达 2500 余年之久,而且,可以肯定,这种情况还会一直继续进行下去。
时而,世人对他的尊崇过甚。时而,人们又对他误解太深。从历史的时空中,总能听到关于他的不同的声音。像雾像风又像雨。
孔子的形象,经过两千多年来不断的改变与塑造,至今已经面目全非,可谓是千人千面。正像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各人的认识不同,孔子的形象亦是千人千面,无法统一起来。
李大钊说:“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象中,潜藏于吾人记忆中,今尚生存于人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李大钊将孔子分成“实在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这种分法,本人倒是比较赞同, 下面简单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一、吃人间烟火食的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人,三岁丧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青少年时期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孔子说他“十五有志于学”。经过刻苦努力,实现了“三十而立”。因为从政的机缘一直未至,于是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之路,即开办私人学堂,开始收徒讲学。
35岁那年,“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齐景公本欲打算重用孔子,但在晏婴等权臣的反对下作罢。在齐三年,孔子非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引起了齐国一些掌权人物的忌惮,他们“欲加害孔子”,孔子空梦一场,匆忙离齐返鲁。这是孔子的第一次求仕。从齐国逃回鲁国后,孔子继续办学。因为在齐求仕挫折的打击,此后好多年,孔子没有再从事任何实际求仕政治活动,而是在从“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一直到“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宝贵岁月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潜心做自己学问上面。孔子50岁那年,终于等到了出山从政的机会。“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在鲁国为官期间,相鲁定公“会齐侯于夹谷”,挫败齐国的阴谋,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做大司寇,杀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最后,在集权公室的斗争中,孔子“堕三都”计划失败。因为失去了鲁国掌权贵族的支持,孔子被迫离鲁出走,这一年,孔子已经55岁。此后,孔子师徒在外流亡14年,辗转各国,希望诸侯见用,可现实却是到处碰壁。在郁郁不得志的奔波中,孔子很快就过了“耳顺”之年。68岁那年,孔子才被允许返回鲁国。晚年的孔子,并没有再去谋求一个政治舞台上的什么具体职务,而是 将自己全部身心沉浸于授徒讲学和整理编辑“六艺”之中,真正达到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给后人留下了读《易》而韦编三绝的千古佳话。
令人惊奇的是,孔子并非如后世儒家或统治者吹嘘的至圣至贤不会犯一点错误的人间神圣。相反,他的身上充满了十足的人间烟火味,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首先,他喜欢美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次,他很喜欢喝点小酒,还很怕管不住自己的酒量。第三,他很注重着装与穿戴,似乎并不拒绝名牌服装。第四,对于异性,他也充满好奇,高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是他能够做到很好地克制自己,认真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第五,他很注重身份地位,出门要有自己的专车,照样在乎名利,只要不是不义之财,他也愿意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而获得。第六,他很有点小资情调,十分喜爱音乐,曾经因为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第七,孔子虽然聪慧执着,但他将自己的做人标准也只是定格为君子的境界,并没有因为自己取得一点成就就忘乎所以。
种种迹象表明,孔子平凡而伟大。平凡表现在他如普通人那样正常地生活;伟大则集中在他对自己理想、目标追求的执着以及对自己修身的践履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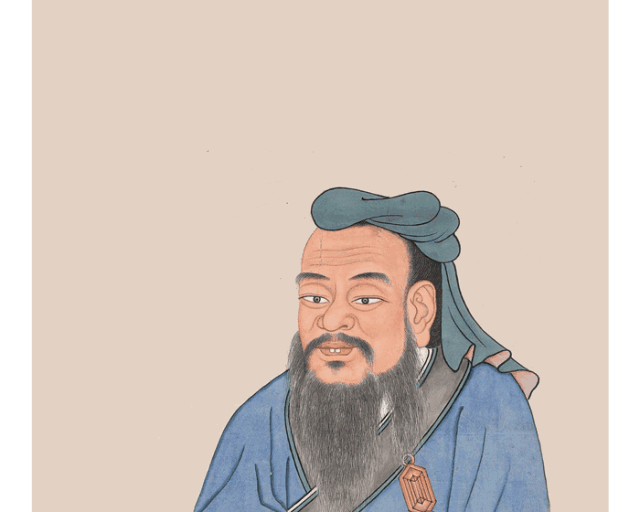
二、吃冷猪头肉的孔子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后,孔子的地位日益变得重要起来。汉平帝时,对孔子的尊崇有了新的发展。孔子和周公一起,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孔子也被封为“褒 成宣尼公”,地位和周公相当,从此被人抬上神坛。东汉时期, 祭祀孔子已经成为每个皇帝必须例行的公事。从汉明帝起,在学校祭祀孔子成为常规,从此孔子作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至圣先师,开始自成一个独立的祭祀系统。从曹魏开始,皇帝或者太子学通一经,就要向孔圣报告,行释奠礼。起初由于孔子在世时官职低,祭礼由太常代行。此后祭孔的规格不断提高。晋代,皇帝或者太子开始亲自行礼。太和十三年(公元 378 年),北魏在京城修建孔庙。从此,孔庙开始走出曲阜,走向全国。南朝梁,就在自己境内修建孔庙。北齐时代,规定在正常的春秋祭祀之外,每月朔日,学校师生必须向孔子行礼。到唐代,对孔子的祭祀,又有新的发展。唐初制礼,曾以孔子为先圣,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为先师。高宗显庆年间,一度曾重以周公为先圣,而黜孔子为先师。后来,又恢复孔子的先圣地位,而将周公作为武王的配食者。这一项制度,到《开元礼》,终于被确定了下来。唐代规定,郡县都要建立孔子庙,祭祀孔子。并且由地方长官担任主祭。这样,孔子作为国家公神的地位,就进一步通过制度方式巩固了下来。孔子的称号,隋唐以前,或是先圣,或是先师、宣尼、宣父。唐代,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宋代,在文宣王前加“至圣”二字;元代,又在至圣前加“大成”字。北宋时曾有儒者建议给孔子加帝号,未获通过。明嘉靖年间,认为称孔子为王,不合礼制。于是经过合议,去掉王号,保留“至圣”,称“至圣先师”。这个称号,一直被清代所沿用。这样看来,孔子虽然身前坎坷,死后倒是已经享受近两千年“冷猪头肉”的供奉。

三、给孔子事业做一个定位
孔子的事业,主要集中在从政、教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三个方面:
第一,他是一个失意的政治活动家。
孔子一生,有着伟大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目标,想要达到“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他之热衷于求仕,不是为了个人“追名逐利”的目的,而是要寻找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机会来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就是主张把治天下的大权还归于周天子。这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但是,当时乱世的客观形势却没有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与舞台,他仅仅只有四五年的时间处于鲁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其他时间里,他最多也只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边缘人”。尽管孔子充满“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的满满自信,洋溢着“天生德予”与“文不在兹乎”的历史使命感,然而现实追求中却处处碰壁。各国当政者也只是将他作为装饰门面的招牌,并不想用他的方案来改革与推动历史的前进。治世的理想没能实现,对他可谓是一个凄婉的悲剧。

第二,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
孔子是春秋时期私人办学最为成功的一人。
在招生范围上,孔子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对接受教育的对象,没有类别限制,只要受教育者愿意真心实意地“志于学”,不论贫富、贵贱、族类、国别、老少,他都可以做到“诲人不倦”。
在教学对象上,“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孔子能够根据学生不同的禀赋、个性、特长、素质、阅历等具体情况,给他们制订相应的教学方案,施以不同的教法,有针对性地给予个性化培养教育,以使他们都能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成为德才兼备的对 社会有用的人才。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在施教过程中,很注意调动弟子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他提倡学思结合,引导弟子在自学基础上深入思考,循循善诱弟子积极主动地思考与提出问题,在此基础上给予指点、引导,而不是采取不顾弟子具体实际情况的“填鸭式”的教学法。
从一定意义上讲,孔子私学不同于今天那些专门培养应试的教育机构,更不是那些以商业运转为模式的专门教育实体,它集学问探讨与修养人生为一体,将个人学习、修身与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实现了充分的结合。它立足于培养人的趣味高尚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能力,让学生对世界上纷纭复杂的事物具有做出正确判断与识别的能力,同时培养人的高贵品性和雍容大气、文质彬彬的气质,养成人的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大学问。这种种因素,使孔子创办的私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以致在当时各诸侯国间都闻名遐迩。私学的红火又使学生越聚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教学相长也反过来成就了孔子的伟大。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用《诗》《书》《礼》《乐》作教材教育弟子,就学的弟子大约有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艺的就有七十二人。至于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要知道,春秋时期的人口总共也不过才有五六百万之多。孔门成才弟子如此之多,难怪当时各国诸侯都对孔子敬而远之了。他们恐惧这股巨大的力量,没有信心借用这股力量,这是他们的悲哀。孔子以一人之力培养出如此众多具有治国安邦本领的弟子。这种成功,从孔子到今天,还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
第三,他是一个学有所成的学者。
孔子是中国文化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一生倡导恢复周礼并在天下奔走呼吁“克己复礼”的孔子,恰恰是春秋时期周礼最勇猛的突破者与否定者。周礼规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孔子不仅到处议礼,更第一个以私人名义公开进行了大规模搜集与整理古代文献的文化工作,开创了中国私人著书立说的先河。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的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
孔子时代,“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王纲坠弛,礼崩乐坏。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导致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文化状况,这就必然造成孔子所能访求到的文化典籍与历史文献,应该是散乱杂芜、残缺不全的。特别是夏商两代年代久远,更令孔子深深地感到“文献不足”的缺憾,所以他叹惜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从 30 岁左右开始,孔子一边教学,一边着手搜集、整理、保存古代典籍的工作。晚年归鲁后,他更是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抢救三代文化工程上面。虽然像周公那样辅佐成王创建一个新天下的理想是无法实现了,虽然那个创建了周朝典章礼制的周公,再也没有来到他的梦中,但是“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却还是那样令孔子心驰神往。《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最终完全被系统整理编纂了出来。正是这项工作,奠定了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儒家鼻祖的地位。
公元前 479 年,病中的孔子预感到自己已经临近了生命的终点,回顾自己拼搏一生的生命历程,再看看这个依然如故昏乱的世道,他具有无限的感慨和无穷的遗恨,不免发出了“天下无道, 莫能宗予”的轻声叹息。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在叩问历史:“泰山就要崩塌了吗?梁柱就要摧折了吗?哲人就要像草一样枯萎了吗?”眼泪也随之落了下来。他还是那样自负,他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是一位“哲人”、一位智者。他本想用自己的本领去“兼济天下”“重建东周”的,可是老天爷不给他这个机会。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有益于后世。他不想成神,而更喜欢人世间的生活。可是,他生前身后的愿望,事实上都落了空。不过,他的仁德的灵魂以及兼济天下、不屈不挠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峨的山峰,一根不朽的栋梁,一块常绿的草地。在夏商周那样的崇神世界中,他发现了人格美以及社会制度的美,从而把人的个体心理欲求同社会的伦理道德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正像老聃把人还给自然一样,孔子把人还给了社会。他对我们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仁”的思想,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和谐发展的平衡共生关系。至于这种理念实践的途径,在他看来,就是应该以“中庸”为思维,用“礼”来治国,积极建立起一个具有良好的道德与法制环境相统一的有秩序的社会。






